【柳氏医派】吉忱公座右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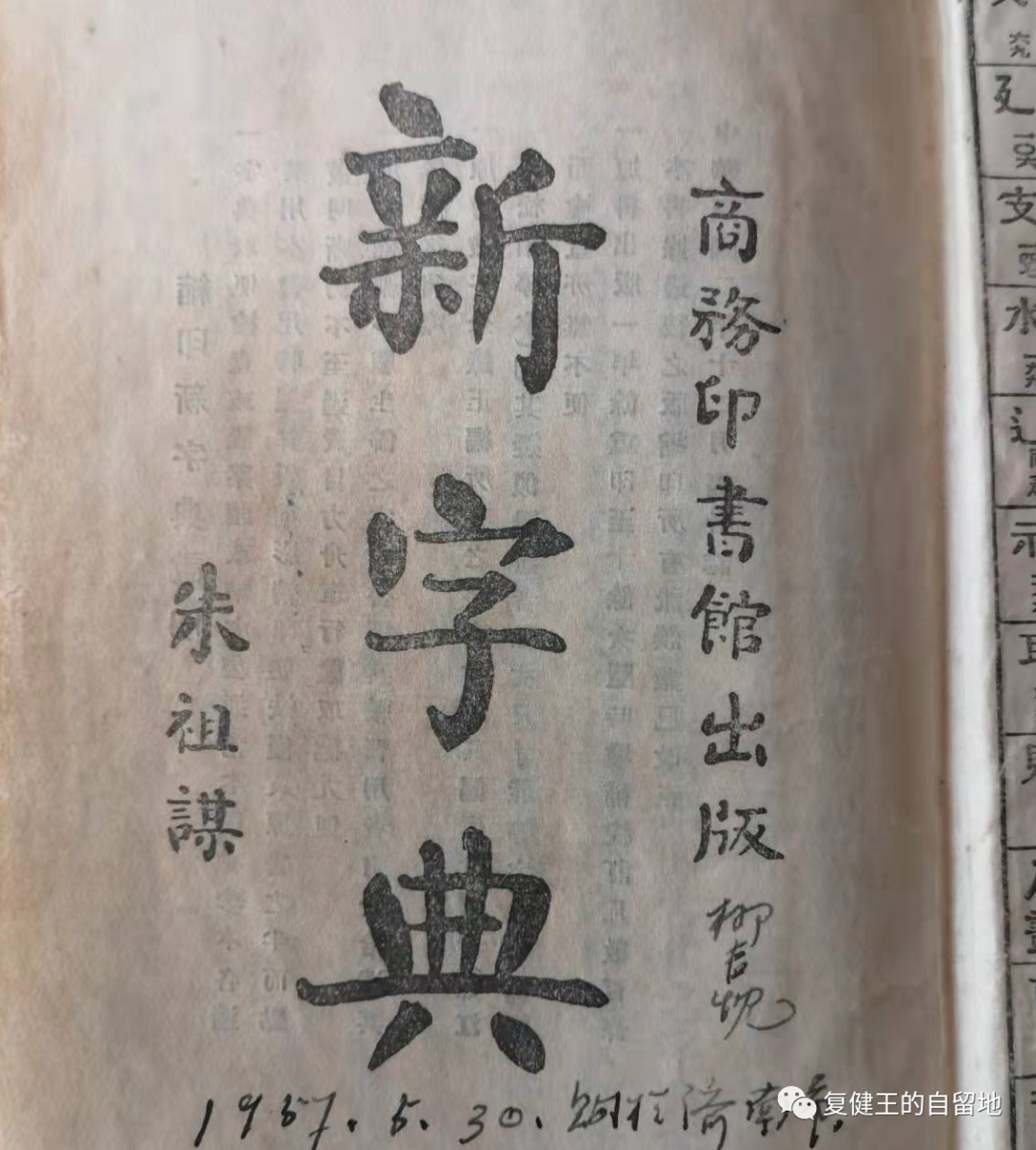
潜心岐黄,继承先贤,攻读《难》《素》,治病救人广流传;
淡泊明志,富贵不媚,权豪不谄,光明磊落处世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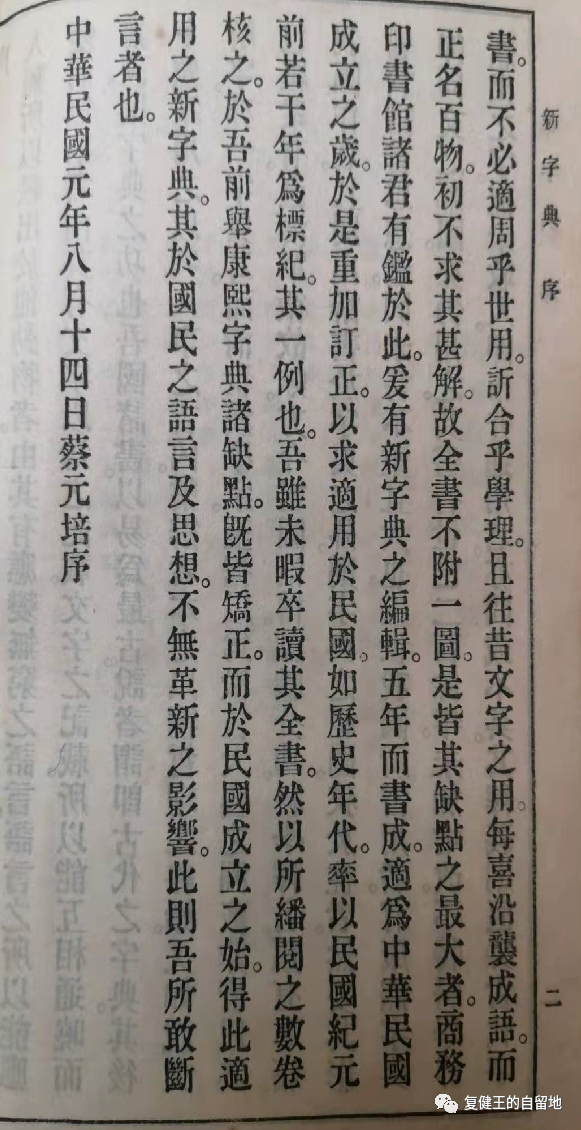
【链接】
柳吉忱及其学术思想简介
柳少逸 蔡锡英
(一)
家父吉忱公,名毓庆,号济生,以字行。一九零九年八月,出生于山东省栖霞县东林村,八岁入本族私塾,较系统地学习了四书五经,从而奠定了扎实的古典文学基础,这为后来学习中医典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及至民国入高小,中学接受现代教育,十九岁毕业于烟台育才中学。
中学毕业翌年,因患类风湿性关节炎回故里。其间曾多次延医,均罔效。后幸得人介绍,请同邑晚清贡生李兰逊老先生诊治,用药仅二十余剂,内服兼外熨,而病臻痊可。诊治间,谈经说史,评论世事,深得先生赏识。于是,先生进言家父习医:“昔范文正公作诸生时,辄以天下为己任,尝曰:‘异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盖以医与相,迹虽殊,而济人利物之心则一也。社会动乱,你就学医吧,一可济世活人,又可养家糊口。”家父欣然应之。从此,便与中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而成为李老先生晚年的入门弟子,赐号“济生”,济世活人之谓也。
先生精通经史,熟谙岐黄之学,兼通律吕及诸子百家。其于医学,深究博览,采精撷华,独探奥蕴,卓然自成一家。先生立法谨严,通达权变,有巧夺天工之妙,常出有制之师,应无穷之变。在随师期间,见先生用阳和汤治疗多种疾病,弗明不解,请师释迷,问曰:“昔日弟子患痹,师何以阳和汤愈之?”师曰:“王洪绪《外科全生集》用治鹤膝风,列为阳和汤主治之首,君疾已愈,当晓然于心,王氏非臆测附会之语也。”又问:“某君腰疾,师诊为痛痹,不予乌头汤,而以阳和汤愈之,恭听师言。”师曰:“景岳尝云:‘此血气逆来则凝而留聚,聚则为痹,是为痛痹,此阴邪也。……诸痹者皆在阴分,亦总由真阴衰弱,精血亏损,故三气得以乘之。’经曰:‘邪入于阴则痹,正谓此也。是以治痹之法,最宜峻补真阴,使气血流行,则寒邪随去。若过用风湿痰滞等药,再伤阴分,反增其病矣。’故今用治痹,非出臆造也。
家父随师诊治,秉烛夜读。在先生指导下,首先阅读了《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原著,并选读了一些名家注释,以冀融会贯通。同时熟诵了本草、药性诸书。其后又学习了《千金》《外台》、“金元四家”、《景岳全书》《温热经纬》《温病条辨》诸家之学。先生以读书者,尚能细心研读,自有深造逢源之妙启迪,质疑问难,深得教诲。先生晚年辑生平所治验案若干卷,付家父。循以治病直如高屋建瓴,节节既得,所当无不奏效,故尽得先生之传。
先生时时以孙思邈《大医精诚》教诲,并以“医之为道,至精至微,明辨而行之,则可以济众,冒昧而施之,适足以杀人”为师训。故家父在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铭记“阴阳之事至微,死生之事至大”,临证中本着胆大心细,行方而智圆之旨,谨守“审证求因、脉证合参”规矩准绳,以医德为重,以仁慈为怀,以济生为己任,以为病人解除疾苦而后乐。
(二)
一九三零年春,曾考入天津尉稼谦所办国医函授班,学习三年。一九三四年,因其通晓英语,应其内兄之聘去广州、香港,在德丰号花边庄任职一年。其后入上海恽铁樵国医班学习,翌年因病返里,一九三八年函授毕业。因受恽氏学术思想影响,家父认识到:对祖国医学一定要推陈出新,引申触长,否则,大有日趋湮灭之虞。所以在五十年代以后,临证师古不泥古,参西不悖中。在辨病与辨证,中西医结合治疗多种疾病中,取得可喜成果。
师承和两次函学,为家父步入医林打开了大门,虽说尚未尽悉中医学之奥旨,但业已登堂入室了。但欲立足于医林之中,谈何容易!一来家境衰落,无资开业行医;二来乡间师资缺乏,周围乡里竞相聘请任教。故栖身于教育行列多年。但牢记师训,执教之暇,兼以行医,不久,声闻渐著,名噪乡里,以教业、医业同时赢得乡邻的信赖。
“七七”事变后,日军进犯中原,侵入胶东,胶东人民开展了艰苦的八年抗战。家父于一九四一年,参加了抗日工作。初任栖东县磁南区中心小学教导主任。一九四二年二月又调任白洋区中心小学任校长。其间曾化名罗林,开展抗日工作。其时敌伪进行经济封锁,医药奇缺,公就利用民间药草和针灸给部队及广大干群治病。其间曾多次短期调部队和抗日政府作医疗工作。
一九四三年十月,为了解放臧家庄镇日伪据点,开设“济生”药房,公以医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翌年臧家庄镇因敌伪起义而获解放。区政府于一九四五年以“济生药房”物资为基础,成立了白洋区医药合作社,公仍任医生。一九四六年栖东县政府将白洋区医药合作社改编成栖东县立医院,一九四七年八月公被任命为副院长。一九五三年栖霞、栖东两县合署,出任栖霞县人民医院副院长。一九五一年去山东医学院学习西医一年,一九五四年调莱阳专区中医门诊部任主任。一九五六年一月六日,以莱阳专区中医门诊部的原有人员和药房的一部分,合并到莱阳专区人民医院,成立中医科,公任科主任。
(三)
在综合性医院建立中医科,这是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的结果。为了促进中医工作的开展,建科同年在内科病房内划分床位,建立中医病案,进行系统的临床观察和中医科研,于四月份总结写出中医典型病例报告,撰写了“中药治疗风湿性关节炎及痛风的经验”、“玄参消炎汤治疗急慢性鼻炎及鼻甲肥大的初步经验”、“越鞠丸合戊己丸治疗消化性溃疡的报告”,及“当归芍药散治疗心脏瓣膜病的初步经验”等学术论文。
时年,莱阳地区“乙脑”流行。家父以温病学说中的卫气营血、三焦辨证防治“乙脑”,疗效尚著。于是医院开展了中医中药治疗“乙脑”的业务学习,他亲自编写教材并讲授。于翌年(1957年)总结写出了“中医对乙脑的认识”、“中医对乙脑的辨证论治”等文章,并以此在全区推广。其间,并根据防治乙脑的经验与体会,补充和修改了其著作《热病条释》。
由于制定了中、西会诊和中西医联合查房制度,及通过对危重病人的诊治,既丰富了学识,又锻炼了胆识。例如,又开展了中医治疗破伤风、急性肝炎、麻疹、菌痢、肾病及癌肿的临床科研,均取得较好的疗效,并总结撰写了“破伤风证治浅谈”、“黄疸证治”、“蝼蛄散治疗肾炎水肿的观察”等论文。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家父在日常医疗实践中,除查阅古籍,向前人学习外,尚打破门户之见,注意向同道学习。别人一方一药的经验亦不放过,即使简单的民间验方,只要疗效可靠,也拿来使用。例如用“乌犀药酒”治疗风湿性关节炎,临床取得显效,其方药就是来源于莱阳老中医迟镇西先生。它如“牛皮消果实治疗产后郁冒”、“黄牛尾根治疗吐血衄血”、“猫眼草膏治疗颈淋巴结核”,及雷公丸、龙虎丸、大力丸、犀黄丸、黄药子酒治疗癌症的经验,均取法于民间验方。此即“到处留心皆学问”也。
昔周岩·《本草思辨录·自叙》尝云:“人知辨证难,甚于辨药;熟知方之不效,由于不识症者半,由于不识药者亦半。证识矣而药不当,非特不效,抑且贻害。”所以有一病,必有一药,病千变,药亦千变。能精悉其气味,则千百药中,任举一、二种用之则通神,不然虽多而罔效。足见“辨本草者,医学之始也。”基于此,家父临证则慎思明辨,然后下笔,补偏救弊,贻误者甚少。得有小暇,犹不辞卷。于诸家本草之书,探本溯源,发其所以然之义。为使药简力专,观察疗效,并对单味药进行探讨。结合临床,撰写了“猪胆汁的临床应用”、“卵黄油治疗慢性胃炎”等临床介绍;根据七情和合,对常用药物的配伍规律进行探索,撰写了“七情和合规范”的论文;根据《伤寒论》小柴胡汤临证加减法及其类方组成规律,对小柴胡汤、桂枝汤、二陈汤及六味地黄汤的药物,变方内函进行探讨,并撰写文章。
他一生桃李遍神州。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零年,尚负责莱阳专区的中医培训工作。曾先后主办了七期中医进修班,为全区培养了大批中医骨干。亲自讲授《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药物和医学史等课。一九六零年受聘于山东省莱阳市中医药学校讲授温病学。从温病学源流及发展、病因病机、辨证方法及方药,均结合个人临床经验和心得而阐发。发挥己见,注重实践,内容广博,由博返约,深入浅出是其教学特点。并示所编“温病舌诊歌诀”,让学生诵记。以“伤寒为法,法在救阳;温病为法,法在救阴”两大法门启迪学生,为临证要点。并倡临证应冶寒温于一炉,方不致墨守成规,胶柱鼓瑟。六十至七十年代又教子课徒十余人,如袁大仲、王树春、赵传松、仲伟臣等胶东名医多出自其门下。
一九五六年,随着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开展,曾举办了多期西医学习中医班。他亲自讲授,使部分西医同道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医。从而促使了中西医的密切合作,解决了临床上许多疑难病症,抢救了大批危重病人。例如在一九五八年“应用大柴胡汤结合静脉输液治疗肠套叠”、“复明饮治疗病后失明”,“中药治疗河豚中毒”,及中西医结合治疗烧伤、破伤风、流脑等均取得显著效果。
(四)
兰逊李公尝祝于医者曰:“贵临机之通变,勿执一之成模。”成模者,规矩也。荀子《劝学》篇云:“木直中绳,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揉使之然也。”无规矩不能成方圆,通变者,运巧也。《劝学》篇又云:“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非生也,善假于物也。”不能运巧,则无所谓规矩。家父栖身医林几十载,深感于神行于规矩之中,巧不出规矩之外,祖国医学理论无一不是常规,临床实践处处有技巧,若津津于常规,则作茧自缚;因证用方,则出神入化。故既要重规矩,又要运巧制宜,庶几左右逢源。
湿与热,是病理变化的反应,又同属六淫范畴。《内经》《金匮》及历代文献均有治疗规范。鉴于湿分内外,热有表里,湿能化热,热能转湿,临证则须运巧。其在临床中,根据季节、时令、气候变化和冷热失常,进行推理诊断、辨证求因与审因论治。临证从整体观念出发,脉证合参,分清虚实,及外邪偏胜或正气偏虚,作为临证处方用药准则,因势利导,拨乱反正而愈病。并根据多年临床实践,归纳出“湿热证治十九法”。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术特点的集中表现。就是对于现代医学所诊断的疾病而言,中医治疗的主要依据仍然在于证。且不可受西医诊断之限,胶柱鼓瑟,束手受败。如静脉血栓形成与血栓性静脉炎,家父认为同属祖国医学“脉痹”范畴。二者虽均为湿热、瘀血痹阻脉络所致,然验诸临床,前者为瘀血阻络而致湿热蕴滞,故瘀血为病的主要矛盾,而湿热则居次要矛盾,治宜活血通脉,佐以清热利湿。一九七三年三月某部队医院接诊一右髋股静脉栓塞引起下肢淋巴水肿患者。处理意见:手术治疗。因病人不同意施行手术,故请家父会诊。病者患部水肿,皮色白而光亮、舌苔黄、脉沉数,为湿热之候;舌质紫暗尚具瘀斑,故血瘀为致病之主证。遂以上法治之,处以当归、川芎、赤芍、牛膝、桃仁、红花、防己、忍冬藤、白芷、丹皮、甘草。服药三剂而痛止,五剂而肿消过半,三十剂后而病臻痊可。血栓性静脉炎,则为湿热蕴结,引起络脉瘀阻,故湿热为主要矛盾,而瘀血为次要矛盾。治宜清热利湿,佐以活血通络。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家父曾接诊一左下肢血栓性静脉炎病人,患病二十余日,几经治疗罔效。查患肢皮肤灼热、潮红,按无凹陷、口干不欲饮、便秘,舌质深红,苔黄腻,脉滑数,遂以清热利湿、活血通络法治之。处以双花、元参、当归、赤芍、牛膝、苡米、苍术、木瓜、黄柏、泽兰、防己、土茯苓、甘草,迭进二十剂,肿势尽消,但患肢仍拘挛灼痛。又以原方去苍术、黄柏、苡米诸药,加鸡血藤续服五剂,病情悉除。
古人尝云:“兵无常势,医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谓之神将;能因病变化而取效,谓之神医。”兵家不谙通权达变,无以操出奇制胜之师;医家不能圆机活法,无以操出奇制胜之功,其理同也。药贵合宜,法当权变,知常达变,着手回春;拘方待病,适足偾事。脑囊虫病,实为临证难愈之疾。家父于前人之验,潜心体验,持循扩充,每屡获效验。如一孙某男性患者,遍体黄豆粒大之圆形结节,质地不坚,推之不移,不痛不痒,且时发痫证、舌质淡红、白薄苔、脉沉缓。经皮下结节活体切片检查,确诊为脑囊虫并发癫痫。即以豁痰开窍、杀虫定痫为法而施治:半夏、陈皮、茯苓、白芥子、胆星、全虫、天虫、榧子仁、郁金、远志、苡米、甘草水煎服,并以磁珠丸佐服。迭进二十剂,结节消失三分之一,痫证仅半月一发。即于原方加竹沥冲服,续服三十剂,皮下结节消失殆尽,痫证偶发。拟健脾化痰、宁心定痫之剂,复进三十剂,诸证悉除,体质康复,一如常人。囊虫病由绦虫的幼虫囊尾蚴,寄生于人体组织而发病。脑囊虫病的临床主证为癫痫、失明。癫痫常反复发作,很少自愈者。故其治法,宜先杀虫理气,后健脾养胃;囊虫病皮下结节,治宜化痰利湿,软坚散结;脑囊虫发作癫痫者,治宜豁痰开窍,杀虫定痫;平时治宜健脾化痰,杀虫散结。总之,以消补兼施,扶正祛邪为大法。
破伤风是一种严重急性外科感染性疾病,祖国医学根据其症状和途径,而有众多的病名。究其病因病机,家父认为皆由血衰不能濡养筋脉,风毒经创口乘隙侵入肌腠经脉,营卫不得宣通而致诸证。甚则内传脏腑,毒气攻心,痰迷心窍,致病情恶化。故立祛风解痉、化痰通络之法。验诸临证,因《医宗金鉴》玉真散祛风之力虽强,而解痉之功则逊,故合入“止痉散”,则祛风解痉之效倍增,合二方加味,立“加味玉真散”(胆星、白附子、防风、白芷、天麻、羌活、蜈蚣、僵蚕、蝉蜕(去头足)、鱼缥胶、钩藤、朱砂、甘草)作汤剂服,临证化栽,每收效于预期。
脑积水,与祖国医学“解颅”一证相侔。因其前卤宽大,头颅若升似斗,故又称“大头星”,实属难愈之证。肾主骨生髓,脑为髓海,肾气亏损,脑髓不足,致后天气血亏损而发解颅。续发于温病者,多由热灼营阴,肝风内动,循行不利,脉络受阻,则青筋暴露而水湿停滞。在临床中,家父以常法内服补肾地黄丸(脾胃虚弱者用调元散),而变通封囟散,拟“加味封囟散”(柏子仁、南星、防风、白芷、羌活、猪胆汁)外敷,治愈小儿脑积水三十余例。封囟散方出《医宗金鉴》,意在疏风、温通、利湿、消肿。加白芷芳香透窍、有疏风、温通、胜湿之功;羌活辛平味苦,平风燥湿,散血解痉,有治“颈项难伸”之能。加味封囟散养血解痉,利湿消肿治其标;设补肾地黄丸补肾益髓、益气养血培其本,标本兼治,内服外敷合用,协同奏效,俾肾强髓密,气充血足,痉解络通,囟封颅合,肿消水除。临床经验,先天亏损、气血两虚者易治,预后佳良;后天温热诸疾继发者难治,预后较差,或见智力不全者。近见三十三岁一青年女子,三十年前温病续发解颅,病情重笃,濒于危殆,经其治愈后,至今神志正常,智力很好。是以后天温热病续发解颅者,亦不能率以预后不良,而贻误病机。
夫六淫七情相同,而罹受之人各异,禀赋有厚薄,质性有阴阳,性情有刚柔,年岁有长幼,形体有劳逸,心情有忧乐,天时有寒热,病程有新久。医者临证,大都通权达变而绝处逢生至于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而严加甄别,以择其精,由博返约,而后臻于精妙者少。家父认为:临证当洞悉天地古今之理,南北高下之宜,岁时气候之殊,昼夜阴晴之变,方能谙达病机,把握治疗。此即五运六气、子午流注学说在临床上的现实意义。祖国医学中的运气学说,它是古代观测物候,气候的基础上演变过来而应用到医学上来的。把自然气候与人体发病统一起来,从客观上认识时间、气候变化与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关系,故运气学说与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关系确是非常密切。例如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烟台地区病毒性肝炎流行,循以常法菌陈蒿汤疗效不著。岁值丙午,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因司天主上半年,在泉主下半年,在治疗上则宗《内经》阳明在泉,湿毒不生、其味酸、其气湿、其治以辛甘苦的治疗原则,主以辛开苦降之剂,佐以甘味健脾之药,于是郁火得清,湿热得除,中州枢转,病臻痊可。其后于一九七二、一九七八年,该地区病毒性肝火又为流行高峰年份,发病季节又均在古历七月份左右,其地支又均分属子、午,为少阴君火司天,“其化以热”,“热淫所胜,怫热至,火行其政”,“四之气、溽署至,大雨时行,寒热互至,民病寒热,嗌干、黄瘅。”俱湿热郁蒸之候,家父乃治以辛苦甘而获大效。是故治病不本四时之规,不审地宜之律,不明标本之理,临证则茫如望洋,无可问津。
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是辨证论治两大法门。家父临证以“识异同”作为辨证手段,使辨病与辨证达到有机结合,从而达到治疗目的。“同病异治”一词,最早见于《内经》,且有《异法方宜论》专篇。至汉《伤寒杂病论》,每篇都冠以“辨xx病脉证并治”或“xx病脉证并治”的篇名,说明了同一疾病,由于证候,病机的差异,而有“同病同证异因异治”、“同病异证异因异治”的不同治法。例如在乙脑、肝炎的治疗中,由于注意了病情的发展,证型的各异,病机的变迁,及用药过程中正邪消长等差异,治以相应方药。
它如冠心病,属祖国医学胸痹,心痛范畴。此病本虚标实、虚实错杂。痰浊为病变前提,气滞血瘀为病变结果。家父临证依据“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和“间者并行、甚者独行”的治则,根据不同阶段,各有侧重。将“通”与“补”两大治法有机的联系和密切结合,或标本兼治,扶正祛邪,或先通后补,或先补后通,或通补兼施。不通则痛,为痛证共同机理。然通有多法:调气以和血,调血以和气;上逆者使之下行;中结者使之旁达;虚者助之使通;寒者温之使通,无非通结而已。本虚应针对阴阳气血、脏腑的不同虚证表现,采取相应的补法。早期病急疼痛剧烈,治标为主,以通为用,治本为辅。病情缓解或稳定,则通补兼施,标本兼治。后期补虚纠偏以固本。此即因病异治循规而运巧也。家父认为:临证若不识标本缓急,妄报芳香开窍之品,滥使活血化瘀之剂,则耗血伤阴,损气败阳,沉弊滋多,适足偾事。
再如对高血压病的临床治疗中,鉴于引起高血压病、眩晕、头痛的主要因素是阳亢,治疗的当务之急是潜阳,故将潜阳法作为一个重要法则(但不是唯一法则)来探讨。鉴于阳亢之由多端,潜阳之法不一,故方药亦因之而异。临床则有泻火潜阳、平肝潜阳、育阴潜阳及治标潜阳法。所谓治标潜阳法,即“阳亢”为标证、兼证的方法。象痰火蕴伏,扰动肝阳者;肝脾同病而阳亢者;及阴阳俱虚而阳亢者,尤其后者,似与理不通,但临证屡见不鲜。阳无阴则不长,阴无阳则不生。肾阳不足或肝旺于上肾亏于下,必波及肾阳,反之亦然。家父拟加味真武汤验诸临证,每收卓效。方由真武汤加石决明、杜仲、寄生、桑椹子等药而成。其特点是附子与石决明等潜阳药物同用。附子为回阳救逆之必须,石决明为镇肝潜阳之要药,二分合用,交济阴阳,以求其平秘。药效殊异,确有异曲同功之妙。如潜阳诸剂,潜降药物首当其冲,对高血压病而见肝阳上亢者,大有攻关夺邑、功效直截之誉。然潜阳药物质地沉重,药性沉降,且临证处方用药剂量较大,长期服用,易出腹泻之弊端,故临床上要中病即止,不可久用。
试观《伤寒论》,仲景用方,炉火纯青,恰到好处。例如小承气汤、厚朴三物汤、大黄厚朴汤,同由大黄、枳实、厚朴组成,用量不同,主药各别,则主治迥异。再如吴茱萸汤在《伤寒论》中三条,阳明篇用治“食谷欲吐”,少阳篇用治“少阳病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厥阴篇用治“干呕、吐涎沫、头痛者”。《金匮要略》二条,一治“呕而胸满者”;一治与前厥阴篇同。仲景之所以异病同治,皆因肝胃虚寒,独阴上逆所致。家父宗异病同治法,运用经方,随证化裁,见效尤捷,体验尤深。如应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治疗痰气郁结之癫、痰火上扰之狂、气逆痰阻之痫、肝气郁结之郁、痰气交阻之瘿证,疗效满意。本方为小柴胡汤的变法,用以治上述诸疾,取其疏肝达郁,宁神除烦,降冲镇逆,化痰散结之功。
(五)
一九五五年家父为山东中医学会会员、理事。后为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会员,烟台地区中医学会副理事长,主任中医师,莱阳市历届政协委员,一九八零年为莱阳市政协常委及文史组副组长。
一九八三年二月因年迈离休。对登门求医者,仍以医德为重,以济生为己任,以解除病人痛苦为最大快慰。诊务之暇,结合个人多年实践,尚著有《风火简论》《济众利乡篇》《中医外治法集锦》《热病条释》、《柳吉忱医疗经验》《脏腑诊治纲要》七书,及“运气学说之我见”、“哮与喘的证治”、“癫狂痫痴的证治”、“崩漏治验”等论文。
其喜咏“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诗句,一生勤奋,堪为师表。栖身医林几十载,虽届耄耋之年,为了振兴中华,振兴中医,而出任山东扁鹊国医学校名誉校长,尚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暮年壮志,决心在有生之年,将己所学,贡献给祖国的中医事业。
【注】本文原载于山海书社《齐鲁名医学术思想荟萃》1995年8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