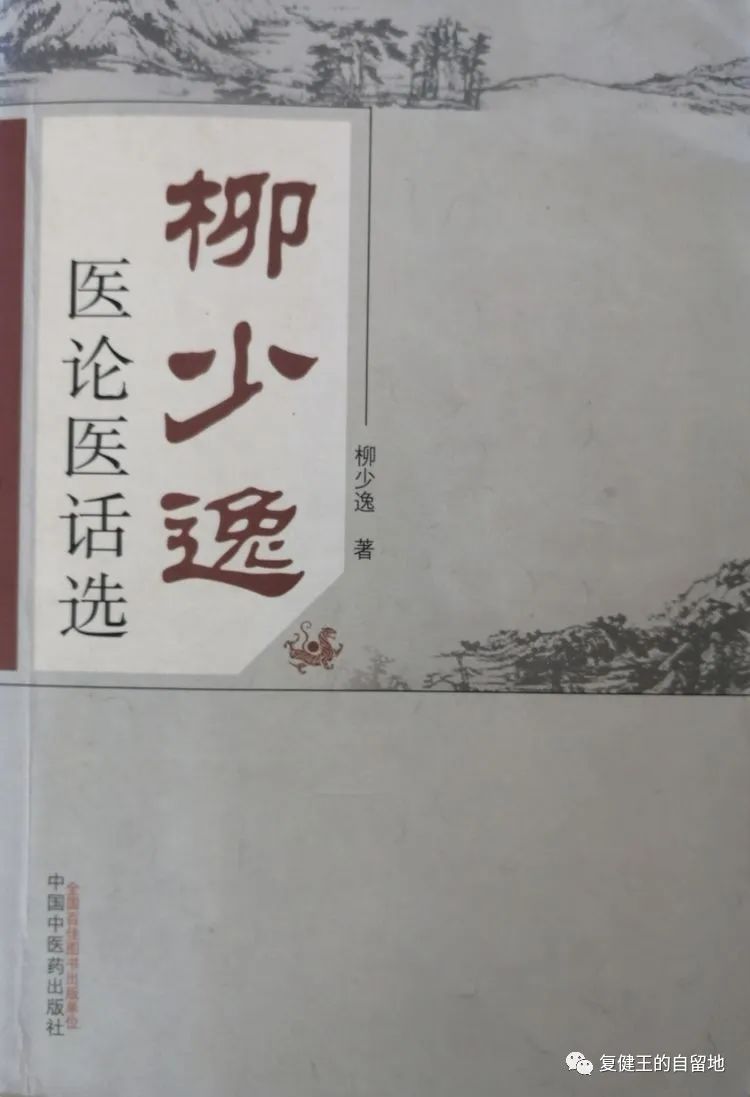【柳氏医派】柳少逸:士人知医是宋代医学繁荣之渊薮

士人知医是宋代医学繁荣之渊薮
柳少逸
昔范文正公作诸生时,辄以天下为己任,尝云:“异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盖以医与相,迹异殊,而济人利物之心则一也。良相燮理阴阳,平治天下;良医燮理阴阳,挽回造化。“盖医之为道,所以续斯人之命,而与天地生生之德不可一朝泯也。”(元·王好古《此乃难知·序》)历代贤哲皆以“儒之从政,医之行道,皆以救世济人为其责任者也”。(徐相任《在医言医》)故清·王敬义有“医之权,诚有通于相业者矣”之论。
儒,通谓孔子创立的学派,又称儒家经学,简称儒学、儒门,而信奉儒家学说的人,称为儒家、儒士、儒人、儒生,而汉称读书人出身或有学问的大臣称儒臣,儒生出身的人称儒吏,精通儒学的宰相称儒宰,儒家群体称儒林。周、秦、两汉用以称某些有专门知识、技艺的人(即术士)亦为儒。《周礼、天官、太宰》云:“儒以道得民。”俞越《群经平议·周官一》云:“儒者,其人有伎术者也。”故而颜师古有“凡有道术者皆为儒”之论。
儒医,旧时称儒生之行医者,邹韬奋尝云:“医生原是一种很专门的职业,但在医字上都加一个儒字,称为‘儒医’,儒者是读书人也。于是读书人不但可以‘出将入相’,又可以由旁路一钻而做医。”俗云:“秀才学医,顺手牵驴”,均形象地说明了“文是基础医是楼”的“儒医”的知识结构。笔者曾撰文“从古今名医简析,谈中医人才的知识结构”,“从中医学的结构,谈黄元御的医学成绩”二文,证实了德高望重,而有真才实学的名中医,都有文史哲的雄厚基础而精于医,他们的知识结构,横跨专业的界河,涉猎到医学、哲学、数学、天文、地理、气象学等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早在宋代已有“儒医”一词,宋·洪迈《夷坚甲志·谢与权医》中有“蕲人谢与权,世为儒医”的记载。
从宋代范仲淹的“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论,说明了宋代全社会对医药学的关注,士人知医成为儒医,形成一种社会风尚,这与宋代科技文化的发展有很深的渊源,同时亦与宋代统治者崇尚医药亦有很大的关系,宋太宗晓于医药,做皇帝前就搜藏效验医方千余首,其于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向全国征集验方,命王怀隐辑成《太平圣惠方》一百卷,收方16800余首,集宋以前医方之大成,为宋初国家出版的重要文献。并亲自作序:“是以圣人广兹仁义,博爱源深”“布郡黎之大惠”“俾令撰集,翼溥天之下,各保遐年,同我生民,跻于寿域。”
宋代官设药局——和剂局,专司药材、药剂的管理和经营业务。《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为和剂局的一种成药处方配本。公元1078~1085年,朝廷诏告天下进献良方,集为《太医局方》13卷,此为《局方》雏型。后经多次重修,于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因改药局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故方书更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该书在《指南总论·论用药法》中有“济世之道,莫大于医;去疾之功,无先于药”的论述,陈承、裴宗元在书成进表中有“以救万民之疾”,“增设疾医之政,以掌万民之病”,“著在简编,为万世法”的赞誉。以此足见宋朝对医药的重视。据传宋神宗赵顼诊断水平号称“上工”,宋徽宗赵佶工于医,“于歧黄家言,实能深造自得。苟使身为医士,与同时诸人较长絜短,医术不在朱肱,许叔微之下”。朱肱:著《活人书》,徽宗朝授奉议朗医学博士;许叔微:宋绍兴壬子(公元1132年)以第五名登科,精于医、活人甚众,集一生已试之效方,著《本事方》,且精研《伤寒论》,著述亦丰。宋徽宗于政和年间,诏令撰《圣济总录》计200卷,载方约2万首,并亲自作序,称“生者天地之大德,疾者有生之大患,方术者治疾之法。作《总录》于以急世用,而救民疾。”而焦养直在重校《圣济总录》序中称徽宗“其仁民爱物之心,斯可谓极矣。”由此可见,宋朝皇帝晓于医,且重视医药事业,是产生儒医的思想基础。故清代《重刊宋本洪氏集验方·序》尝云:“宋祖宗之朝,君相以爱民为务,增设惠济局,以医药施舍贫人,故士大夫多留心方书,如世所传《苏沈良方》,许学士《本事方》之类,盖一时风尚使焉。据传名相王安石自述《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由此可见,由于皇帝对医药的空前重视,一大批名士介入医学领域,促进了北宋医药的发展,形成了“儒医”阶层的思想基础。同时形成了名士撰集方书的风尚,如公元998年广南史陈尧叟著《集验方》,公元1026年宋仁宗为之作序;1047年王衮《博济方》;1075年的《苏沈良方》;1101年的《史载之方》; 1119年闫忠孝撰《闫氏小儿方论》;1123年王贶撰《全生指迷方》;1133年张锐撰《鸡峰普济方》;1143年许叔微撰《普济本事方》;1170年洪遵撰《洪氏集验方》;1174年陈无择撰《三因方》;1178年杨倓撰《杨氏家传方》;1196年王璆撰《是斋百一选方》;1237年陈自明撰《女人大全良方》;1253年严用和撰《济生方》;1264年杨士瀛撰《仁斋直指方》。上述撰集者多为进士及第之文人达官,其集方以简、便、验的医药特点而广为应用,促进宋代医药事业的发展。而今天大中专中医教材《方剂学》中,选自两宋方书中的方剂约占六分之一,这充分说明研究两宋方书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注】本文选自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柳少逸著《柳少逸医论医话选》2015年4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