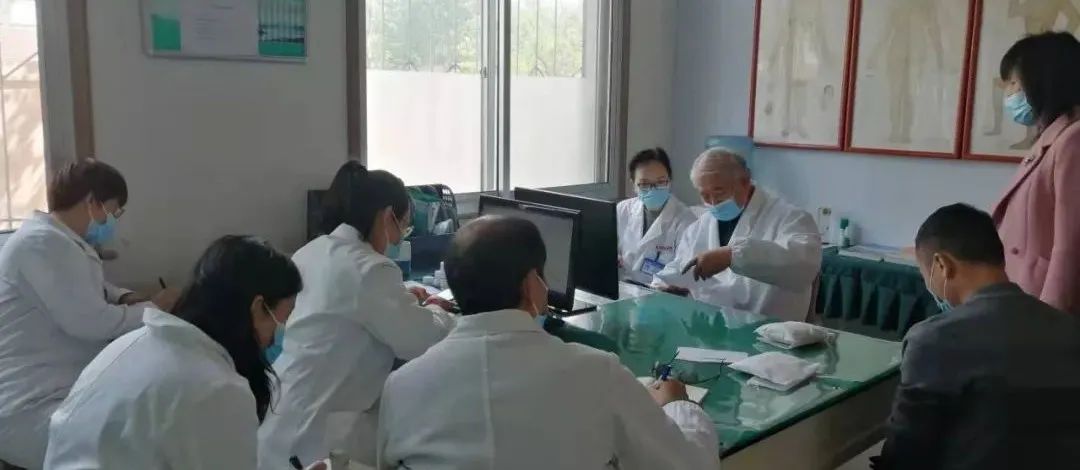【柳氏医派】柳少逸:电视访谈答记者问(1)

记者:您出生于山东栖霞东林一耕读世家,从小就随父亲习医。请问,您的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如何培养和指导您学习中医的?对您一生有何影响?
柳少逸先生:1943年3月,我出生于山东栖霞东林一耕读世家。家父吉忱公(1909~1995),六岁入本族私塾,至民国接受现代教育,其后入天津于稼谦国医班、上海恽铁樵国医班学习。曾拜晚清贡生儒医李兰逊先生为师,从而走上济世活人之路。“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入胶东,家父投笔从戎,参加抗日工作。其时敌伪进行经济封锁,医药奇缺,遂利用地方中草药和针灸推拿等法给部队战士及广大干群治病。解放后,先后任栖东县立医院院长、栖霞县人民医院业务院长、莱阳专署中医药部主任、烟台市莱阳中心医院中医科主任。自1954年起,受莱阳地区专员公署委任,负责胶东地区的中医培训工作,为半岛地区培养了大批中医骨干。一部分成为创办山东中医学校的骨干教师,一部分成为组建地、市级医院中医科的骨干中医师。1960年又受聘于山东省中医药学校讲授温病学。20世纪60~70年代又教子课徒数人,家父以其从医及教学的切身经历,探求培养中医人才的模式,故山东诸多名医多出自其门下。
家父吉忱公是我一生的老师。学中医要有“背功”。我童年时,让我背诵“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那个时代,中、小学学习环境比较宽松,在高小时就让我背诵《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汤头歌诀》、《八法用药赋》、《频湖脉诀》等中医启蒙读物。读中学时寒暑假即给我讲授他的《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经》、《温病条辨》、《时病论》、《中医医学史》讲稿。并在我高中毕业时,并已全部讲授了中医高等院校一版中医教材。
习医之初,家父即以清·程芝田《医法心传·读书先要根》语训之:“书宜多读,谓博览群书,可以长识见也。第要有根底,根底者何?即《灵枢》、《素问》、《神农本草经》、《难经》、《金匮》、仲景《伤寒论》是也。”在我熟读中医典籍以后,又指点选读后世医家之著,并以清·刘奎“无歧黄而根底不植,无仲景而法方不立,无诸名家而千病万端药症不备”语戒之。每晚授课后,必读书至子时,方可入睡。
历代医藉,多系古文,就字音字义而言,又涉及文字学、训诂学、天文历法学等古文化知识。一些古籍,若周诰殷盤,佶屈聱牙,泛泛而学,可谓苦也,故我亦有“定力”欠佳时。有一次对家父低声语云:“何谓‘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症多?’”家父笑云:“昔清·陈梦雷尝云:‘九折臂者,乃成良医,盖学功精深故也。’汝读书无笃志,仍不明为学之道也。朱熹尝曰:‘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莫在于读书。’‘读书之法无他,惟是笃志虚心,反复详玩,必有功耳。’汝当熟知:博览群书,穷理格物,此医中之体也;临症看病,用药立方,此医中之用也。不读书穷理,则所见不广,认症不真;不临症看病,则阅历不到,运动不熟。体与用,二者不可偏废也。又当明清·顾仪卿《医中一得》之语:‘凡读古人书,应先胸中有识见,引申触类,融会贯通,当悟乎书之外,勿泥乎书之中,方为善读书人。’此法谓之“心悟”、“神读”,待汝临证时,方可悟苏轼‘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之意也”。言毕,又谓:“昔吾师李兰逊公曾以元·王好古‘盖医之为道,所以续斯人之命,而与天地生生之德不可一朝泯也。’明·龚信‘至重惟人命,最难却是医’等语为训。”在随父习医时,庭训多在旁征广引说理间。这些话语,深深地印在脑海中,永不晦暗。从而造就了我“至重惟人命,最难却是医”之立品:“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之学风。所以,家父课徒先从中医典籍起,强调必须打下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方可言医。
其后,我将其部分医案整理结集,名《柳吉忱诊籍纂论》,其讲稿整理成篇,名《内经讲稿》、《伤寒论讲稿》、《本草经讲稿》、《温病讲稿》。
习医之初,家父吉忱公即以清·黄元御“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草》”之训导之。认为此乃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也,后之欲为方园平直者,必深究博览之。这是一种临床思维方法,非是“厚古薄今”。“理必《内经》”,是因《内经》理论是中医基础之渊源;“法必仲景”,是临床要辨证论治的;“药必《本经》”,不是只用那三百六十味药,而是运用药性理论,即性味归经、升降浮沉及其配伍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