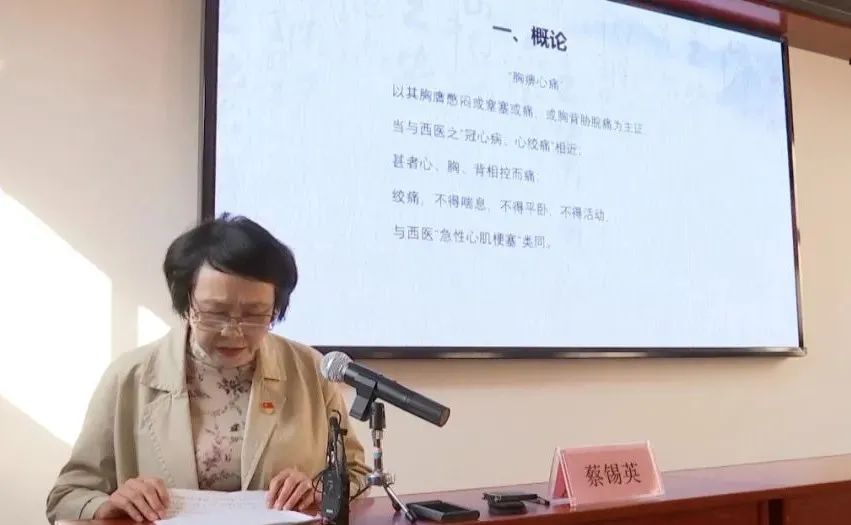【柳氏医派】蔡锡英:浅谈水液代谢的系统观及临床思维方法

浅说水液气化的系统观及临床思维方法
一般系统论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把生物和生命现象的有序性和目的性同系统的结构稳定性联系起来:有序,因为只有这样才使系统结构稳定;有目的,因为系统要走向最稳定的系统结构。基于现代系统论的许多重要原则,诸如整体性原则、相互联系原则、有序性原则、动态原则。几乎都可在中医学中找到许多原始思想,本文试从人体水液气化的系统观及其临床治疗中的思维方法,阐明其所寓有的系统论许多重要原则。
一、 从“肾者水脏,主津液”谈肾主水液的系统论思想。
《素问·上古天真论》云:“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素问·逆调论》云:“肾者水脏,主津液。”说明了肾中精气的气化功能,对于体内津液的输布和排泄、维持体内津液代谢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素问·经脉别论》云:“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此段经文说明了在正常的生理情况下,水液的气化,是通过胃的摄入,脾的运化和转输。肺的宣散和肃降,肾的蒸腾气化,以三焦为通道。输布至全身,经过气化后的津液,则化为汗液、尿液和浊气排出体外。而肾中精气的蒸腾气化。实际上是主宰着整个水液气化的全过程。因肺、脾等内脏对水液的气化功能,均赖于肾中真元的蒸腾气化功能。
水分清浊。清者上升,浊者下降。清中有浊,浊中有清。说明了水液气化是一个复杂的生理过程。涉及多个脏腑的一系列生理功能,反映了水液运行全过程中,构成了一个气化功能系统,人体寓有一个有条不紊的水液运行构造。
脾“为胃行其津注液”。脾胃通过经脉一方面将津液“以灌四旁”和全身;另一方面将津液上输于肺,此即脾的散精功能。同时,小肠的泌别清浊的功能,与尿液的量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素问·灵兰秘典论》云:“小肠居胃之下,受盛胃中水谷而分清浊,水液由此而渗入前,糟粕由此而归于后,脾气化而上升,小肠化而下降,故曰化物出焉”,由此可见,小肠的泌别清浊的功能是脾胃升降功能的具体表现。故此,饮入于胃。在中焦脾胃及小肠的作用下,将水中之精上输上焦达肺,水中之浊通过下焦而达肾。此即:“中焦如沤”、“中焦主化”之意。
清中有清,清中有浊。肺主宣发和肃降,具有调节腠理、司开合之功。在肺主气、司开发的作用下,将清中之清(水中精微物质),外达肌表,“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即“上焦如雾”、“上焦主纳”之意.而残废的水液或为浊气呼出体外,或化为汗液通过“玄府”排出体外。而清中之浊者,又在肺主肃降,通过三焦的通道而达肾,故又有“肺为水之上源”之说。
浊中有清,浊中有浊。通过三焦通道归肾之水,在肾阳的蒸腾气化作用下,将浊中之清通过三焦的通路,重新上输于肺,而浊中之浊,在肾的气化作用下,生成尿液下输膀胱。《素问·灵兰秘典论》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焉”。说明了膀胱的贮尿和排尿功能又全赖肾的气化功能,所谓膀胱的气化,实际上是隶属于肾的蒸腾气化。下焦残废的水液排出体外全赖于此,此即“下焦如渎”、“下焦主出”之意。
《素问·灵兰秘典论》云:“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决,疏通之意;渎,即沟渠之形。决渎即通调水道。鉴于三焦在经络属少阳,内联三阴,外联二阳,具有沟通水道,运行水液的作用,是水液升降出入的经路。且全身水液是由肺、脾胃和肠,肾和膀胱等诸多脏腑的协调作用下完成的。其特点必须以三焦为通道,才能正常的升降出入。《灵枢·营卫生气》篇的“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读”,则概括了三焦是“脏腑之外,躯体之内,包罗诸脏,一腔之大府也”。故三焦气化功能在水液气化过程中起重要的协调作用。
鉴于“肾主水液”主要是指肾中精气的蒸腾气化功能。它主宰着整个水液运行的代谢活动。而三焦又主持诸气,总司全身的气机和气化。即三焦是气化升降出入的通道,又是气化的场所。元气是人体的最根本之气,又根于肾。通过三焦而充沛于全身,故《难经·三十八难》有“三焦者,气之所始终也”;《难经·三十八难》有“元气之别焉,主持诸气”;《难经·六十六难》有“三焦者,原气之别使也,主通行三气(宗气、营气、卫气),经历五脏六腑”之说。故而整个水液代谢过程,是以“肾主水液”为核心,以三焦气化为内容构成一个系统。其中寓有深刻系统论重要原则――整体性原则、相互联系性原则、有序性原则、动态性原则。
二、从“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谈系统方法在临床中的应用。
全身气化功能障碍,临床上主要有水肿、淋证、遗尿、消渴等。今就水肿一证,说明系统方法的具体运用。
(一)中焦主化与脾主为胃行其津液
《素问·水热穴论》云:“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上下溢于皮肤,故为胕,胕肿者,聚水而生病也。”说明了胃阳不足,脾阳不振,“中焦主化”失司,“脾主为胃行其津液”功能障碍,以致水饮溢于肌肤.则为痰饮,水肿。临床上则宗《金匮要略》之“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法。如慢性肾炎而见眼睑浮肿及踝部水肿者,可予以苓桂术甘汤(《金匮要略》:获苓、挂枝、白术、甘草),或防已茯苓汤(《金匮要略》:防己、甘草、白术、黄芪、大枣、生姜),或肾气丸(《金匮要略》:地黄、山茱萸、山药、泽泻、茯苓、丹皮、桂枝、附子)而化裁调之,以冀气化而水行。
若肿而伴恶心呕吐者,为脾虚运化无力,可与小半夏加获苓汤(《金匮要略》:半夏、生姜、茯苓),以和胃止呕,引水下行。
若身肿腰以下为重,按之凹陷不起,伴有脘腹痞闷,纳呆便溏,小便不利者,此中阳不振,健运失司,中焦失化之重症,当予实脾饮(《济生方》:附子、半夏、白术、甘草、白扁豆、莲子肉、砂仁、薏苡仁),或加黄芪、桂枝以益气通阳,或加故纸、肉桂以温肾助阳而加强气化。
若遍体肿,胸脘痞闷,小便赤少,或大便秘结,苔黄腻,脉数者,为水饮之邪郁而化热,湿热壅滞三焦之象。宜疏凿饮子(《世医得效方》:商陆、泽泻、赤小豆、椒目、木通、茯苓皮、大腹皮、槟榔、生姜、羌活、秦艽),以分利湿热;若大便秘结,腹满不减者,可合已椒苈黄丸(《金匮要略》:防已、椒目、葶苈、大黄),以助攻泻之力,而导邪下行。
(二)上焦主纳与肺主行水
《灵枢·决气》篇云:“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是指肺的宣发卫气,散布精微的作用。若风邪犯肺,肺之宣发卫气,调节腠理开合功能失司,毛窍闭塞不能将气化后的津液化为汗液排出体外,症见眼睑浮肿,恶寒发热,小便不利者,当以风水论治,予以越婢汤(《金匮要略》:麻黄、石膏、生姜、大枣、甘草)化裁。若肺失宣降,不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而伴全身浮肿者,以疏风清热,宣肺行水之法,予越婢加术汤(《金匮要略》:越婢汤加白术)化裁。
若风邪犯肺,肺失宣发肃降,三焦气化受阻,而兼见小便不利,舌红苔黄,脉数者,为外有表邪,内有里热之证。宜表里双解之剂,予以麻黄连轺赤小豆汤(《伤寒论》:麻黄、连轺、杏仁、赤小豆、大枣、生梓白皮、生姜、甘草)化裁,以冀解表散邪,清热利水之功。
肺开窍于鼻,鼻与咽通而连于肺,故鼻与咽为肺之门户,又有“鼻为肺之窍”,“咽为肺之门户”之说,外邪袭肺多从鼻而入,故风邪犯肺,有郁久化热之势。而见咽喉肿痛者,宜宣肺解毒,清咽消肿之剂,予以麻黄连轺赤小豆汤合五味消毒饮(《医宗金鉴》:双花、野菊花、公英、地丁、紫背天葵)化裁。
《金匮要略》“水之为病,脉沉小,属少阴”。是指水肿病,脉沉小,与少阴肾有关,是属正水范畴。为不能蒸腾气化,上焦主纳和肺主宣发肃降、通调水道功能不足而致。临床多见初起眼睑浮肿,继则全身肿胀,按之有凹陷,大便软,小便少,脉沉小之证,故宗《金匮要略》“腰以上肿宜发汗”之旨,当顾及肾阳,宜用麻黄附子汤(《金匮要略》:麻黄、甘草、附子)以温经发汗。
(三)下焦主出与肾主水液
“肾主水液”是指肾脏具有主持全身水液气化,调节体内水液运行呈稳定状态,故称作肾的“气化”作用。“下焦主出”是“肾主水液”功能的组成部分,是狭义的“肾主水液”的功能,即被脏腑组织利用后的水液(水中之浊,清中之浊者)以三焦通道而归肾,经肾的气化作用分为清浊两部分,清者,再经三焦上升,归于肺而散于全身:浊者变成尿液,下输膀胱,从尿道排出体外。如此循环往复,以维持人体水液气化、运行和输布。
若证见面浮身肿,腰以下尤著,按之凹陷不起,腰肢重,四肢厥冷,尿少,舌质淡胖,白苔,脉小或沉迟无力者,为肾气衰微,阳不化气之证,则宗《金匮要略》“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法,宜温肾助阳,化气行水之剂,予以济生肾气丸(《济生方》:地黄、山药、山萸肉、丹皮、茯苓、泽泻、炮附子、桂枝、牛膝、车前子)合真武汤(《伤寒论》:炮附子、白术、茯苓、芍药、生姜)化裁。
若病延日久,肾阳久衰,阳损及阴,而出现肾阴虚为主的病证时,临证以水肿反复发作,神疲心烦,腰酸遗精,舌红,脉细弱为辨证要点,宜滋肾益阴,兼以利水之法,予以左归丸(《景岳全书》:熟地黄、山萸肉、杞子、山药、丝子、川牛膝、鹿角胶、龟板胶)合猪苓汤(《金匮要略》:猪苓、茯苓、阿胶、滑石、泽泻)化裁。若肾阴久亏,水不涵木而致肝肾阴虚、肝阳上亢,以浮肿肢颤、眩晕、头痛为辨证要点者,治当育阴潜阳,化气行水之法,予以左归丸合三甲复脉汤(《温病条辨》:炙甘草、干地黄、生白芍、麦冬、阿胶、生牡蛎、生鳖甲、生龟板)化裁。
若肾气虚极,中阳衰败,浊阴不降而见神倦欲睡、恶心呕吐,甚则口有尿味者,宜温阳化气,解毒降浊之法,予以附子泻心汤(《伤寒论》:附子、黄连、黄芩、大黄)合小半夏加茯苓汤化裁。
腰为肾之外府,若肾病日久,肾络瘀阻,而见腰痛、水肿诸证者,当活血通络,渗湿利水,予以当归芍药散(《金匮要略》:当归、芍药、川芎、茯苓、白术、泽泻)加味,或桂枝茯苓丸(《金匮要略》:桂枝、茯苓、丹皮、芍药、桃仁)加味治之。
(四)三焦气化与水道出焉
《中藏经》云:“三焦者”“总领五脏六腑,营卫经络,内外上下左右之气也,三焦通,则内外上下皆通也,其于周身灌体,和调内外,营左养右,导上宣下,莫大于此者也。”此即三焦在经络上属少阳,内联三阴,外联二阳,入病之道路,出病之门户,且“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又为“水谷之道路也”,故在水液气化过程中,三焦起重要的协调作用,称之谓“三焦气化”。
若水湿之邪,浸渍肌肤.郁于少阳,致少阳枢机不利,三焦气化失司,水道壅滞,而证见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心烦喜呕,小便不利,肢体浮肿者,治宜调达枢机,化气利湿,予以柴苓汤(《沈氏尊生书》:小柴胡汤合五苓散)化裁。
若水湿之邪,浸渍肌肤,三焦气化壅滞,以致全身浮肿不退,小便短少,肢重,胸闷脘痞,泛恶,苔白腻,脉沉者,宜健脾化湿,通阳利水之法,予以五皮饮(《华氏中藏经》: 生姜皮、桑白皮、陈皮、大腹皮、茯苓皮)合胃苓汤(《丹溪心法》:苍术、厚朴、陈皮、甘草、生姜、大枣、桂枝、白术、泽泻、茯苓、猪苓)化裁。
结语
祖国医学水液气化系统,寓有系统论的许多重要原则。不难看出,人体水液气化与肺、脾胃、小肠、大肠、肾、膀胱、三焦等脏腑有着密切关系。而肺的宣散,脾的运化和转输,肾的气化,则是调节水液气化的中心环节。其中,以肺为标,以肾为本,以脾为中流砥柱。肾的气化作用是贯穿于水液气化的始终,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以“肾者主水”,“肾为水脏”为核心,以三焦为通道构成了一个系统。是以系统的整体性、相互联系性、有序性和动态性原则构成的。因此,临床上,则需围绕这些原则运用系统论的思维方法,对水液气化失司而致的病证,而选方遣药,随证化裁,而不刻意于机械地分型。本文开宗明义在谈水液气化的系统观及其所寓有的系统论思想,对水液气化失司(具体讲水肿一证)的证治,也只是谈到临床的思维方法,故不属纯临床的证治之论。
【注】本文原载于柳少逸/蔡锡英等《杏苑耕耘录》1992年版,后被《蔡锡英医论医话选》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