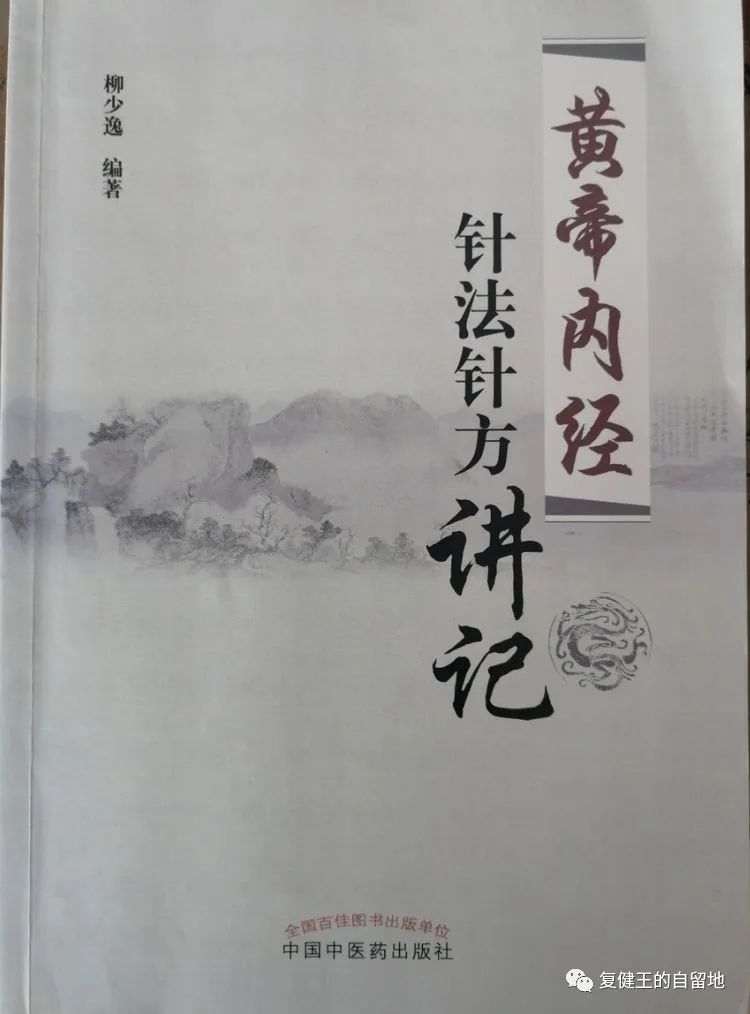【柳氏医派】柳氏医经学派针灸术“七大针刺法则”之二:顺其自然

【按】法则,即准则、规则之谓。针刺法则,即针刺必须遵循的准则,即针刺之大道。概而论之,即顺应自然法则。诚如《灵枢》所云:“有道以来,有道以去,审知其道,是谓身宝。”柳氏医经学派针灸术有“刺必辨证、顺应自然、补虚泻实、调气治神、行针候气、因人而异、深浅时间适宜”七大基本法则,分而享之。
柳氏医经学派针灸术“七大针刺法则”之二:顺其自然
《素问·八正神明论》云:“黄帝问曰:用针之服,必有法则焉,今何法何则?岐伯对曰:法天则地,合以天光。帝曰:愿卒闻之。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风之气,气定乃刺之。”该篇复云:“是以天寒无刺,天温无疑。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郭空无治,是谓得时而调之。”《灵枢·逆顺肥瘦》篇云:“黄帝问於岐伯曰:余闻针道于夫子,众多毕悉矣,夫子之道应若失,而据未有坚然者也,夫子之问学熟乎?将审察于物而心生之乎?岐伯曰: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数,法式扴押,乃后可传焉。故匠人不能积尺寸而意短长,废绳墨而起平木也,工人不能置规而为园,去矩而为方。知用此者,固自然之物,易用之教,逆顺之常也。黄帝曰:愿闻自然奈何?岐伯曰:临深决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循掘决冲,而经可通也,此言气之滑涩,血之清浊,行之逆顺也。”《灵枢·四时气》篇云:“黄帝问於岐伯曰:夫四时之气,各不同形,百病之起,皆有所生,灸刺之道,何者为定?岐伯答曰:四时之气,各有所生,灸刺之道,得气穴为定。故春取经血脉分肉之间,甚者深刺之,间者浅刺之,夏取盛经孙络,取分间绝皮肤。秋取经腧,邪在府,取之合。冬取井荥必深以留之。”《灵枢·终始》篇云:“春气在毛,夏气在皮肤,秋气在分肉,冬气在筋骨,刺此病者,各以其时为齐。”《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篇云:“黄帝曰:以主五输奈何?岐伯曰:藏主冬,冬刺井;色主春,春刺荥;时主夏,夏刺输;音主长夏,长夏刺经;味主秋,秋刺合。是谓五变,以主五输。”上述经文表述了“用针之服,必有法则”,“必候日月星辰”;“天寒无刺”,“天温无疑”,“月生无泻”,“月满无补”;“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数”;“四时之气,各有所生,灸刺之道,得气穴为定”;及“冬刺井”“春刺荥”“夏刺输”“长夏刺经”“秋刺合”诸刺法,均表述了“法天则地”,即顺应自然规律乃针刺之大法。此即《内经》“人与天相生,与日月相应”的天人相应的系统整体观在中医针刺学中的体现。于是有了“冬刺井穴方”、“春刺荥穴方”、“夏刺输穴方”、“长夏刺经穴方”、“秋刺合穴方”的五季应五输穴之针法、针方。
《素问·诊要经终论》云:“黄帝问曰:诊要何如?岐伯对曰:正月、二月,天气始方,地气始发,人气在肝;三月、四月,天气正方,地气定发,人气在脾;五月、六月,天气盛,地气高,人气在头;七月、八月,阴气始杀,人气在肺;九月、十月,阴气始冰,地气始闭,人气在心;十一月、十二月,冰复,地气合,人气在肾。故春刺散俞,及与分理,血出而止,甚者传气,间者环也。夏刺络俞,见血而止,尽气闭环,痛病必下。秋刺皮肤,循理,上下同法,神变而止。冬刺俞窍于分理,甚者直下,间者散下。”诊要,即诊治疾病的要道;经终,谓十二经脉之气终绝。此段经文表述了诊察疾病的要道是要与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及其与针刺方法的关系。如正月、二月,天气开始升发,地气开始萌动,这时候的人气在肝;三月、四月,天气正当明盛,地气正是华茂而欲结实,这时人气在脾;五月、六月,天气盛极,地气上升,这时人气在头部;七月、八月,阴气肃杀,这时人气在肺;九月、十月,阴气渐盛,开始冰冻,地气也随着闭藏,这时人气在心;十一月、十二月,冰冻而阳气伏藏,地气闭密,这时人气在肾。由于人气与天地之气皆随顺阴阳之升浮沉降变化规律,故而有适时之刺法、刺方。此即“春夏秋冬,各有所刺,法其所在”之谓也。所以春天的刺法,应刺经脉俞穴,及于分肉腠理,使之出血而止,如病比较重的应久留其针,其气传布以后才出针,较轻的可暂留其针,候经气循环一周,就可以出针了。此法名“春季刺病法”,方以法立,故方名曰“春季刺病方”。夏天的刺法,应刺孙络的俞穴,使其出血而止,使邪气尽去,就以手指扪闭其针孔伺其气行一周之顷,凡有痛病,必退下而愈。此法名曰“夏季刺病法”,或名“夏季刺病方”。秋天的刺法应刺皮肤,顺着肌肉之分理而刺,不论上部或下部,同样用这个方法,观察其神色转变而止。此法名曰“秋季刺病法”,或名“秋季刺病方”。冬天的刺法应深取俞窍于分理之间,病重的可直刺深入,较轻的,可或左右上下散布其针,而稍宜缓下。此法名曰“冬季刺病法”,或名“冬季刺病方”。
【注】本文选自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柳少逸著《<黄帝内经>针法针方讲记》2017年8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