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道】《大医鸿儒·柳少逸世医传承录》:文是基础医是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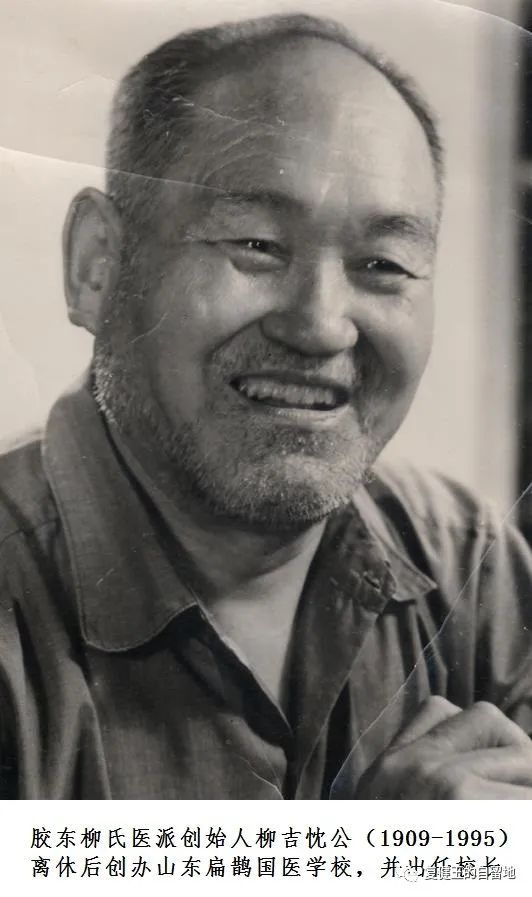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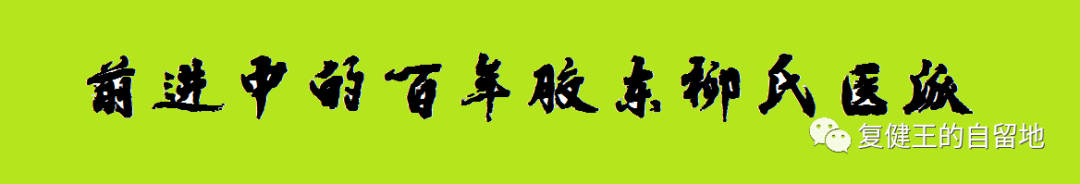
文是基础医是楼
中医说“治病必求其本”,本在哪?“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以培中医之本。”柳少逸一语中的。
柳少逸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药学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和根基,弘扬传统文化对提高中医药学术水平和临床疗效以及人才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认为,无论何种类型的中医药人才,都必须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可惜,建国以来由于受西医学模式的冲击,人们普遍忽略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与培养,导致当前中医药人才乏人乏术的严重局面。因此,中医文化研究自然成为亟待发掘的一个巨大课题,也成为有识之士研究的热潮。柳少逸于1995年主持召开了“山东省中医文化学术研讨会”,以其研究成果,成为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文化分会理事。
学国学 坚持自信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它自成体系的东方文化,明显地与其他体系的文化有区别。故弘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当代人无可推卸的责任。“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接触研究国学典籍。”柳少逸认为。
早在1906年,章太炎先生在《国学讲习会序》中有“夫国学者,所以成立之源泉也″的论述;邓实在《国学讲习记》中,有“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的记载。中医学为国粹,中医典籍为国学重要内容之一。故承扬中医药事业,亦为“一国之学以为国用”之谓也。自十九世纪以来,弘扬国学与颠覆传统之争一刻未曾停止过。若说数典忘祖是偏見,连典都不读的人是无知。
民国初期,著名学者胡适与辜鸿铭都有着深厚的西学背景。胡适是洋书读多了,把国人的毛病看透了,更加自卑;而辜鸿铭是洋书读多了,把洋人的毛病看透了,更加自负。所以鄙視国学,就会失去文化自信;就会生出精神漂泊的卑微心态。那些只读过几本中医教科书,又学些西医知识的人,从而把中医的毛病看多了亦不足为怪了。故而有志于中医药事业的人,当以中医学为国粹而自信。
研读《黄帝内经》和《古文观止》等传统文化书籍,有助于我们学习和更好地理解中医学的。这是因为古医籍文义深奥,有些字多音多义,古体假借情况甚多,且无断句。若无坚实的古文基础,则难以登堂入室。如学习《易经》了解了阴阳变化、消长盈虚的规律,从而更有助于理解和掌握中医的阴阳学说。“医文并重,不仅提高了文学素养,而且加深了对经文的理解和记忆。”
柳少逸何来此观点?原来,他通过对古今54位中医药学名家,尤其对春秋战国至晚晴时期著名的29位医家的研究,发现这些名老中医有着深厚的文史哲等中国传统文化学养,有的还精通琴棋书画,以致“上穷天纪,下极地理,中知人事”,故有“文是基础医是楼”之说的结论。并撰文“从古今名医简析谈中医人才的知识结构”。
医学鼻祖岐伯,不但精通医学,而且是“司日月星辰,阴阳历数,尔正尔考,无有差贷”的通才。这是古代中医人才的模式,故中医学又称“岐黄之学”。
其后,历代德高望重有真才实学的名中医,都有雄厚的文史哲基础而通晓医学。医术高明而有“起死回生”之术的扁鹊秦越人;举孝廉创辨证论治大法的医圣张仲景;知识渊博,通晓经书,精于外科的三国名医华佗;王叔和官至太医,编著《脉经》,攥修仲景之书;通晓四书五经,因患风疾而志于医,著《针灸甲乙经》的皇甫谧;著《肘后方》的葛洪,广览群书,诸子百家之言,下至杂文,诵记万卷,好神仙导引之法,炼丹以期遐年,所著尚有《神仙传史集》《五经诸史》《百家之言》;学识渊博,被誉为“山中宰相”的陶洪景,不但精于医学,而于天文,历法、诗文诸方面亦有较深的造诣;被尊为“药王”的孙思邈,通百家之说,善庄老之学,兼好释典;身为太傅令的王冰,好医学,注释经典;以第六人登科,官至翰林的许淑微,尚是一位研究《伤寒论》医学家;金元时期有学识渊博,在医学上各有突破的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丹溪四大家;明清两代又有李时珍、王肯堂、张介宾、傅山、柯琴、陈修园、徐大椿等诸多有成就的医家。他们大都是精于经、史、子、集,博于天文,历法、律吕而有造就的医家。
在柳少逸撰写的“从中医学的结构谈黄元御的医学成就”一文中,他通过对黄元御的生平、知识结构、医学成就、成才基础和道路的探索,充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药学的深刻影响和深远意义,形象说明了这位医学巨匠“文是基础医是楼”的知识结构。
溯起源 汲取精华
中国有句话叫作“文以载道”。中医这个“道”载于何处?就是载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柳少逸分析,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知识体系——儒、道、释,都和中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儒家有关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正确认识与论述;佛家关于人心性的认识和论述;道家及天文诸家有关人与自然关系和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与论述,都对中医理论构架的形成与发展起着核心性的奠基作用。因而中医的哲学思想、思维模式、名词术语,乃至与医学有关的方方面面无不涵容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
柳少逸认为,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的《黄帝内经》,其构筑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就是在充分吸收春秋战国时期的科学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形成的。就内容而言,中医药学横跨专业的界河,纵横捭阖于不同领域,集医学、哲学、数学、气象学、物候学、天文学、历法学、地理学于一体,从而形成以医学为主要内容的百科全书。“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是《内经》的核心理论,而“形与神俱”,则是医学追求的终极目的。究其渊源,它源于阴阳五行学说,是古代医学家在天人相应的宏观世界基础上创立的。
中医药学不仅广泛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也以巨大的包容性涵盖了许多外域乃至现代医学科学知识,甚至在早期形成时期就蕴含许多现代先进理论的萌芽。如《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及明清崛起的温病学派著作,就是在不断吸收同时代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上丰富起来的。
就其理论体系而言,中医药学可分为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药物学和方剂学几个方面。柳少逸在“浅谈五运六气学说中的系统思想”一文中,从五个方面探讨了运气学说所反映的系统性思想。认为现代系统论的许多重要原则如整体性原则、相互联系原则、有序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几乎都能从运气学说中寻找其原始思想。这正好说明,系统理论相互联系原则是客观的、普遍的,它可以应用于一切科学领域。
柳少逸分析,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文化的影响,不断地交融渗透,进而形成了有着诸多学科而之间又相互影响的独特文化体系。中医药学正是受这种趋势的影响而发展的。如儒、释、道等诸子之说,其追求的“中庸之道”、“中和之美”、“庄禅意境”、“恍惚虚无”均不同程度影响了中医药学,特别是中医的情志治疗学以及后世的音乐导引、气功疗法等均直接脱坯于此。中医养生实际上基本就是脱源于道儒养性修心的哲学观。
强根基 创建理论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影响了从哲学、文学、美学、音乐、医学的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其论点指出,人与自然界的协调统一和个体对整体的适用性,是天地万物的规律,也包含了人类作为个体存在于大自然的普遍性。柳少逸研究发现,由天地间阴阳五行之道及三才、干支、河洛等象数哲学,结合在人体生命中从自然界运气的变化(物候、气候的规律变化),统一到从人体生命活动随之而至的同步变化;从子午流注的周期交接规律,进而指出人体疾病的治疗观和生命的养生观;适应自然,适应整体,达到一个协调的稳态,因而获得健康长寿的目的。因此,柳少逸创建的中国象数医学理论体系就是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应运而生。
因此,他认为,无论是《周易》(包括《尚书·洪范》)还是《黄帝内经》,无论是阴阳还是五行,都是采用了象数思维的模式。象数思维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思维方式会有很大不同。在中华文化背景下,人们理解中医的理论概念相对很容易,对“上火”、“寒包火”、“阳虚”之类的词语耳熟能详,这是因为人们往往对与自己思维方式相一致的东西感觉某种天然的亲切,从而对之接纳度、融会贯通能力相对就强。
中医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医文化是中医医疗保健方式及其相关文化的总和;狭义的中医文化指中医文献与中医有关的古典文学和医案医话。中医药学依赖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一般理论指导,天人合一,三才同物就是实证。同时,中医药学的某些独特发现和发明也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如五运六气学说、子午流注学说。只有在中国传统文化指导下的中医医疗活动,才能获得应有的疗效。中医药学药提高临床疗效,必须回归到辨证论治的轨道上来。
柳少逸认为,中医药学作为一种多学科应该责无旁贷地纵横交织起来,进而寻求更高质量的发展。纵观中医古籍,无论哪个流派,甚于学术观点争鸣较甚的医家,其用药或主凉或主热,但疗效都不错,这种情况在当今临证亦可寻见。实际上,中医药学的源流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的观点争论,只是论治的不同而已。无论哪种治法,所依据的亦不离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内容。所谓“法无定法,唯象唯物”就是这个道理。外治法、内治法、或针或药或采取综合治疗,都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一种治病途径。
“文是基础医是楼”,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疗效是一种医学能否生存延续的关键。中医传承几千年,医籍浩如烟海,被中医治疗的人群当以万亿计,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中医还要加以改造重建?过去的名老中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注重理论联系实践,掌握中医辨证思维体系,因地制宜处理各种病情,才能做到药到病除,取信于民。
柳少逸认为,在不少中医人的观念中,没能认清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医子文化密不可分的源流关系,没能认清中医学术体系的本质和特点,没能认清不懂中华传统文化,就不可能学到中医真谛的利害关系。因此,当务之急就要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强化中医根基。同时把准中医学术方向,扭转异化;改革中医教育,理顺中医药管理体制。这才是中医药发展的治本之道。
